这座南海小镇,如何与台风共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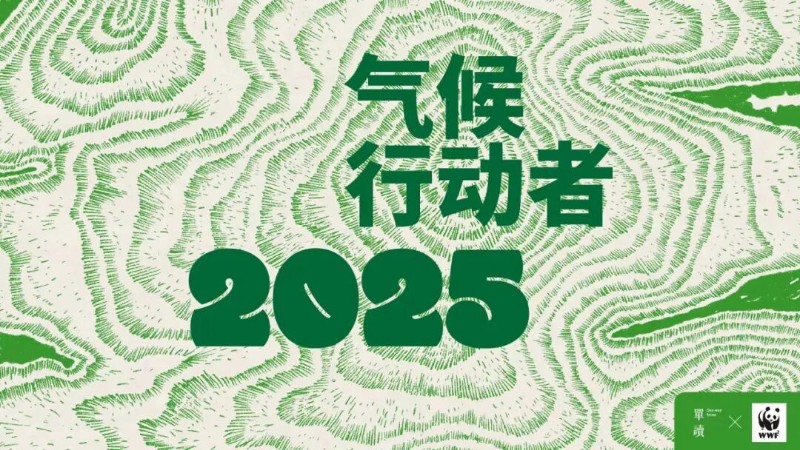
伴随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,极端天气事件正频繁重塑我们的生活图景。
从碳排放目标到能源转型方案,关于应对气候危机的谈判在国际会议厅中持续进行。而在更微观的层面,气候危机的力量并不抽象。它落在中国南端的海岛小镇——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,落在每一场台风之后的废墟与重建中。
从十一年前的“威马逊”,到去年的“摩羯”,风席卷过街巷、吹倒甘蔗田;也是在同一片土地上,风推动着一座座白色风车旋转发电。对于翁田镇附近的居民们来说,风几乎从不缺席,它既是摧毁房屋的力量,也是点亮家园的能源。
陌那的作品《风口的小镇》,以台风与风电并存的海岸为现场,记录这座“与风共生”的小镇:渔民、追风者、捕风人、重建者——他们在风暴的前线继续生活,经历全球气候变迁最具体的震荡,也在风能的浪潮里重新找到希望与方向。
本篇作品在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与单读联合发起的气候行动者 2025——“再生”创作征选项目的支持下完成。该项目已连续举办三年,旨在激励创作者,以文字与影像为媒,重新想象人与自然、地球、能源的关系。而陌那带回的风口小镇现场,让我们看到了更具象的“再生”的可能。
木兰湾的风依旧在吹。
摧毁与再生同时发生,“在敬畏、承受、对抗、利用与共生之间,人们持续校准着与风的关系”。
风口的小镇
作者/摄影:陌那
台风遗迹
在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,造访海南文昌翁田镇,紫檀树遮蔽了主干道。阳光透过碎叶,洒在街边喝茶的人身上。他们分两拨,坐在粉色或绿色的塑料椅子上,年轻人在奶茶店打游戏,年长些的则爱光顾老爸茶店,选一个有风的位置,一个人发呆,几个人围坐吹牛,一壶柠檬茶坐一下午。
风,是这里的常客,也是绕不开的话题。正在雷州半岛或三亚登陆的遥远台风,给小镇带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,人们的记忆就又被拉回去年,以及十一年前——这里是 2024 年台风摩羯和 2014 年台风威马逊登陆的地方。它们是有气象记录以来,秋季登陆我国的两个最强台风。
风暴在西北太平洋巡游,旋转数千公里,在登陆时释放积聚的能量。而登陆点的位置,如同命运的骰子,在大气中摇晃不定。
小镇的居民见惯风浪,也理解偶然和运气。秦朗是 80 后,平时卖净水器,兼顾帮人开挖机,常在老爸茶店跟朋友小聚。他喜欢讲一个离奇的故事——风刮来了一笔钱。去年 9 月 5 日,台风摩羯登陆的前一天,他爬上家门口的大树修剪枝干,突然来了灵感:下一期彩票,该不会跟台风有关吧?他想到 20 多种可能,从“台风打人”“台风把树打倒”等词汇里,选了“超强台风”,用软件“翻译”成数字。买了 5 块钱的彩票,据他说,中了头奖,拿了 4 万多奖金。
话语被头顶的风扇吹散,茶见了底,就自行续杯,杯底大颗的白砂糖浮浮沉沉。一起喝茶的渔民朋友,网名“人生如梦幻”,五十多岁,边玩手机边聊,也是位没受风灾影响的幸运儿。他皮肤黢黑,每天出海,跟 5 个渔民一起拉网抓鱼,底薪 3000,抓到鱼就多赚。超强台风过境,听说曾有渔船被吹上房顶,但他只是给船主打工的,不操心。
来台风没法出海,他还有抖音里的世界可去。在网上,梦幻哥是个有 8 块腹肌的美男子,发了 300 多个视频,在不同的 AI 背景里微笑,看上去最多 20 岁。

翁田镇夜晚的琼剧表演
小镇上少见红绿灯,踏板电动车是主要交通工具,灵活地穿梭车流。遇到广场上表演琼剧,电动车直接就停在马路上,司机们排成一片 VIP 观影区,只留下窄窄的车道。
在这个仅有三万多人的小镇,步行二十分钟,几乎能到任何地方。人们走路慢悠悠的,闲适松弛,烟火气弥漫蒸腾。镇上至少有十几家茶铺,转过一个街角,总能发现一个卖槟榔的摊子,和一位“槟榔西施”。集贸市场是人气中心,镇郊的街道上,也有超市、按摩店、海鲜粥宵夜,一家台球厅灯火通明。
断掉的旧电线垂落下来,跟树藤缠绕在一起,角落里歪斜的路牌上,贴了招建筑工人的广告。台风留下的痕迹,已经被编织进日常的经纬。
但在陈果眼中,摩羯的威力仍然清晰。他之前是货车司机,退休后加入村委会,跟 7 个村干部搭班子,管 1168 户人,每周都要进村。
骑电动车驶过村道,烈日之下,荒地长满了杂草,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,在村里,五六十岁已算年轻。田里水牛在散步、洗澡,鸭子乱叫,黄狗左顾右盼,目送过往的车辆。
歪斜的栅栏、椰树上叶子的折痕,指出摩羯行进的方向。被薅光叶子的枯树,瓷灰色的枝干伸向天空。

摩羯过后,电线杆被吹歪

村道旁有许多枯树
陈果知道,村口的甘蔗地是新种的,旧的去年全吹倒了,农户一点钱都没赚;东一块西一块的焦黑土地,散落着炭化的椰子,这是村民焚烧风灾垃圾的地方;一家老宅的屋顶,一半灰色,一半橙色,是旧瓦被吹得满天飞,又买了新瓦补上。一些老房子倒了,台风后建房政策放宽,到处都在盖新房。


台风过后,四处都在盖房
工人不够用,陈果母亲住的老宅,屋顶吹坏了,等了三个月才有人修,排队期间就用黑布盖住挡雨。
也有老人无力维修,一个 93 岁的老头,独自住在老宅。房子塌了一间,不影响他睡觉,做饭,就任它塌着,阳光从屋顶的洞照下来,一地都是碎瓦。

有两种瓦片的房顶

93岁爷爷家被台风吹塌的房间
在老人的记忆里,几十年前的台风,只会毁庄稼,不像威马逊、摩羯这样猛烈,毁树毁房屋。不过比起修房子,老人更惦记门口被吹折的树。邻居把树砍了盖新房,占了他的地界,老人家不乐意。在村里,人们最在意公平,遇事总要说道说道,把“姜太公在此,天地分界”写在墙上。
但是,风不讲人间的道理,也不守神仙的规矩,说也没处说。


村里人们把“姜太公在此,天地分界”写在墙上
摩羯“君临”
台风摩羯一出生,就是“庞然大物”。UP 主历史飞鹰,喜欢从更宏大的尺度上理解风,他把视角拉上太空,用卫星云图观看地球上的风云变幻。对他来说,台风是一个个活过的生命,梅花、杜苏芮、贝碧嘉、蝴蝶、韦帕、桦加沙……他做视频,为一个个台风“战神”立传,经历巅峰、挫折、减弱和陨落,就像在看不同的人生。
比如摩羯,它是南海的传奇风王,诞生时,它的脚下是 30 多度的温暖洋面,这是能量的温床。季风水汽不断涌入体内,它翻越吕宋岛的高山,对流卷绕中,罕见的极低风切和超高海温,让它打开了风眼。
历史飞鹰还在读大学,年轻的气象爱好者们交流起来,会聊到台风的“颜值”。一个体现“暴力美学”的台风,有着深邃的风眼,这是高强度的象征,只有极少数台风才拥有;此外,还会有圆润的核心,协调的雨带。
美丽的外表下,酝酿着危险。在历史飞鹰看来,摩羯达到了南海台风的强度上限,既恐怖,又“完美”——这是大自然的现象,风只是按科学规律生成、涌动,并不关心人类视角中的善恶。
近年他在网上云追风,发现“奇葩”的台风变多了,温暖的水会养出强有力的台风,它们的部分能量,来自于人类工业文明排放的温室气体。排放源分散在全球,时间跨度几十年,灾难却会在某个具体的、脆弱的角落爆发。
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,全球强热带气旋的比例、最强热带气旋的最强风力,将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而增加。
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实验室主任王春在,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,“在全球变暖 2°C 的情况下,台风可能要么不来,来了强度可能刷新历史。”这意味着,摩羯的“君临”并非孤立的极端事件,而可能更频繁地出现在未来气候图景中。
与历史飞鹰一样,5612 也是气象爱好者,两人曾结伴“追风”。这是圈子里的小众爱好,5612 正为考取大气科学专业复读高三,将追风视作理解台风的必经之路。他形容自己“骨子里带点疯狂”,像摩羯这样的超强台风,有人觉得追它是找死,5612 却感到兴奋。班上的同学笑他:有好几十个女朋友,每年从海上不远万里来,他跑几千公里去追,双向奔赴。
他追过“烟花”“暹芭”“梅花”,台风的登陆点极难判断,接连的失误、错过,暴雨泡了手持气象站。2024 年追摩羯时,他已经学会了看台风数值模型,锁定海南翁田镇。轮渡提前停航,他只好在徐闻角尾乡——摩羯的二次登陆地点感受风暴。
入住海边民宿,天慢慢黑下来,风开始变大,从正常吹气的“呼呼”声,到刮过窗户的尖啸声,最后变成火车开过的轰鸣声。卫星云图上的完美风云,落地成了毁灭性的物理力量。5612 躲在离门窗七八米远的墙角,依然感到本能的恐惧,害怕风掀了门,把自己吸出去。全村断电,楼在震,地板在震,一片黑暗里,突然整片天都红了,是变电器爆炸了。
追风者收集的一手台风数据,有些已经应用于科研,影像资料则用于科普,提高防灾意识。5612 想理解关于台风的一切,比如,想要进入超强台风的风眼。风眼内是下沉气流,无风,透过它可以看到阳光和天空,周围一圈云墙绵延十几公里,绕着身体旋转。
台风特殊的路径摆动、与山脉之间的相互作用、离奇的结构、登陆前的突然爆发……在一个气象规律动荡的时代,超越人类的自然力量和愈发不确定的气象未来,吸引着追风的人。“在进入核心圈之前”,5612说,“你永远不知道会面对什么。”


一个小台风之后的晚霞
循环
从太空云图回归地面,一个台风被普通人记住,往往意味着被搅扰、中断、乃至连根拔起的生活。
说起 2014 年的威马逊,一些翁田人的共同记忆,是童年破旧的老宅、满天飞的瓦片,躲在八仙桌下面发抖,祈祷关公保佑。这个梦魇,改动了一些人的人生脚本,成了后来赚钱、盖屋的动力。强风推倒祖辈的瓦房,瓦砾之上,一些平房立了起来,台风倒逼小镇升级防御。
十年如同一次轮回,摩羯跟威马逊一样,都从一场宁静、美丽的晚霞开始,却造成了 4 省 741.5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,倒塌房屋 2900 余间,直接经济损失 720.3 亿元。
这一次,人们有了更多防风经验,抢桶装水、备充电宝、在窗户上贴胶带、修剪树枝、用棍子顶住门。心理上也有准备,知道在超强台风面前,防御的徒劳与无力,“一点办法也没有,你只能看着它摧毁”,养殖户王力说。
他在翁田镇田南村养东风螺和东星斑,这是年夜饭上的“好运菜”,寓意团圆美满。田南村靠海,村民大多做水产养殖。十四年前,赶上大学生创业能贷款,王力贷了 10 万块,返乡创业,威马逊把他刚建好的养殖场整个掀了。
他从头再来,每个养殖池的成本一两万,10 年时间,王力从五六十个池子,做到两百多个。去年摩羯,他知道防不住,和兄弟、工人一起撤离,去地势高处的平顶房躲风。睡不着,大伙就聊天,不能提损失、十年心血、难过、压力,能聊的只有重建计划。

王力的水产养殖场

空养殖池
那天一片世界末日景象,分不清雨和风,窗户上蒙了一层疾驰的白雾。摩羯的威力被拍摄下来,在网络上疯传,成为奇观。一整条街都是狂舞的树,疯魔了一般,枝干像伸向四面八方的手。电线杆倒掉,线上有电火花。摩天轮的车厢乱晃,如同手链上抖动的珠子。海景房的落地窗,真的落地了。空调外机挂在最后一根电线上,一下下敲打窗户,敲得人心慌。椰子树被打趴到地下,一个反弹,又站了起来。遮天蔽日的乌云里,透出一线天光。
风暴过后,没水没电没网,现代文明的信号消失了,废墟之上,古老的社会连接被激活,支撑小镇度过危机。买东西要现金,小孩子攒的硬币都被翻了出来。没有现金的,就靠熟人之间刷脸赊账。失去屋顶的女人,躲到邻居姐妹家里暂住。路道被堵死,村民出门带一把砍刀、电锯,自己动手开路。

摩羯刮过近一年,村道上仍然到处是刮断的树木
人们排队打井水吃,小孩饿了等不及,一位母亲就捡柴火、接雨水煮饭,桶里满是树叶。镇上出现了新的生意,发电机给手机充电,收取“充电费”。电力抢修结束,全镇自发欢送外地抢修队,一位民宿老板娘说,“灾后都没哭,送他们走的时候哭了”。
风过后,王力的养殖场,已经面目全非,顶棚板子被掀了十几张,连通大海的抽水管坏了,24 小时运转的抽水泵也报废了,暴雨稀释了养殖池的盐度。起初他还开发电机,烧柴油,每天成本 2000 块。水质很难维持,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盐度从正常的二三十格,掉到七八格,池里的东风螺和东星斑一批批死去。
清路障、丢垃圾、扔被水泡坏的家具、重建厂房,王力每天光着膀子,顶着烈日干活。手机成了玩具,唯一的用处就是夜深时,翻看家人的照片,给在镇上中学教书的妻子,写一些发不出去的微信。
村里秀美的大树,被台风撸去了树叶,只剩下核心的树枝。生活也一样,生存之外的都被削减,王力从前是骑行爱好者,为了恢复生产,他卖掉了摩托,只留下护具作为念想。
据他了解,同行大多亏了几十上百万,很多人本就是贷的款。外地来做养殖的,有人直接跑路,当老赖。也有人把妻子儿女带回老家,安顿好,再回到海南的厂房里,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清债。

树木被撸去树叶
王力发现近年天气恶劣,“好像变天了一样”——夏天高温异常,厂房达到 40 多度,干活满身大汗。村里的老人也害怕,除了威马逊,没见过这么大的台风。去年王力损失了 90 多万,但他还是选择重复威马逊之后的脚本,再度重新来过,又贷款一百多万。每一次重建,都加深他与脚下土地的羁绊。
他三十多岁,已经是三个儿子的爸爸,离不开故土。当地的文化,讲究“落叶归根”,几乎每个村都有宗祠。王力的本家祠堂,摆了 18 代的匾额。小儿子刚学会走路,他就带着一起上山祭祖,告诉儿子他们的来处。
祖屋,是一个宗族的根,祖先盖的第一个房子,供奉着先人。早年间,当地有离乡闯荡的风潮,风把人吹去南洋,人们又寻根而回。哪怕 20 年不回村的人,也要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。
“祖宗在这里几百上千年了,大家一起住在这里”,卖净水器、爱喝老爸茶的秦朗,家里老房子旧了,就重新盖,台风把它打坏了,秦朗花了三十万再重建,“赚的钱几乎都花在房子上,修了三四次,大半辈子就过去了”。
在他看来,这是后人的责任,“没有祖宗就没有我”,不可能离开家乡,去没有台风的地方谋生。秦朗说:“如果根(老家)没了,树叶长得再好,都没有一个支点。”
秦朗的朋友阿城也是本地人,做文昌鸡养殖。铁管焊接的鸡棚被台风吹塌,鸡压死了一大片,下雨又冻死一些,14000 只死了约一半,损失 20 万,找挖机挖了个大坑,全埋了。
阿城离不开家乡,“你不能跑,跑去哪里呢?不继续你干嘛?”对他而言,重建不是选项,是唯一的路。台风每年都有,手机里一堆 APP,关注着每一个台风的形成、路径、登陆点。风险一直存在,他们可以选择的,是不在焦虑中过日子。今天挣 300,朋友们晚上吃顿烧烤就花光,天塌了再说。
超强台风三年来一次,还是十年来一次,被秦朗和阿城视作一种命运:“它过来也没办法,听天由命,反正你人在,怕什么?”

海岸,风车
距翁田镇约三十公里的木兰湾,有一片风车海岸,不远处是亚洲第一灯塔。这片海域,自古就是风的国度。
木兰湾是世界第二、亚洲第一的“急水门”,风大浪急、礁石密布。因此海难频发,木质渔船碎成一块块烂木头,被冲上海滩,得名“木烂头”,古人以为是海妖作祟。明朝时,附近的七星岭上,建了一座斗柄塔,用来震慑海妖——或许这是古人视角里的风。
海南的神话,也与风有关,冼夫人巡防海疆、平定海匪时,就是挟风雨自天而降,狂风巨浪将海盗船尽数掀翻。

木栏头灯塔

1954 年,木兰灯塔建成,承担起为船只导航的功能。当地人为了防风避险,不住海边,附近一片荒芜。从“震慑”到“规避”,是这片海岸与风相处的古老模式。
彭青是现任守塔人,据他讲述,守望灯塔,曾是一份孤独的工作。以前的守塔人,顶着风雨,晚上点亮煤油灯,早上再去熄灭。生活艰苦,收集雨水喝,采买物资要去附近的镇上,坐牛车过沙滩,走五个小时。曾有工作人员得了阑尾炎,无法及时救治,去世了。
如今,风变成了景观资源,风车让风显形,变得可以观看。这片风车海岸,已经成为网红旅游地,彭青从塔上望下去,游人络绎不绝,节假日的车能堵好几公里。
一个后备箱集市自发聚集起来,卖小食冷饮、露营设备。流浪全国的咖啡师,开着房车来摆摊,会认识另一个流浪咖啡师,尝尝对方的冲泡手艺。也有假日从海口赶来的摊主,主业卖电动车,副业木兰湾练摊。

晾晒渔获
这里传统利用风的方式,是渔民看风使帆、晾干渔获,盐户晒制海盐,而现在,兜风者们占领了海岸。
风掌控四季更替,气候变化,也掌控人的心情。吹软风,树叶摇动;吹清风,旗子飞舞;吹微风,青草摇动不止;吹和风,草地波浪起伏;清劲风,河面出现水波。风的等级再往上加,超过 6 级,就是强风、劲风、大风、烈风、狂风、暴风、飓风。
韩风目前是一个全职的“兜风者”,这是他的微信昵称,爱风的自由。韩风年近 50,之前做物流,在海南和内陆之间运送轿车,现在失业了。他每天的生活,就是开着电动车踏板车兜风。除了车架和外壳,电机、电池、刹车被他换了个遍,车的速度能飙到 130 迈,最远的一天,他骑了 500 公里。
威马逊台风登陆时,他在三亚开着车遛弯儿。那时的路灯上,都装着风力发电机,台风直接把机器刮了下来,他捡到两个。发电机至少二十斤重,扇叶的直径有一米八,汽车后备箱放不下,电瓶车的车尾也装不上,就在家里放着。
韩风常去木兰湾风车海岸兜风,漫无目的地骑行,看着巨大的风车放空,脑子里想,风车的叶子转个两圈,就能把自己的电瓶充满。
风车海岸上有个充电站,他和兜风的朋友经常一边充电,一边喝茶。从后备箱掏出套娃钛合金杯,接上踏板车的外接电源,三分钟就能烧开一壶水,走到哪里,哪里就是移动茶室。
风车捕捉风,而相机捕捉风车。这里旅游业红火,有商业旅拍摄影师,也有摄影爱好者,查好银河起落的时间,一时兴起,就约起伴来拍星空。
风的环流绕过地球,带来远方的讯息。海滩上会出现矿泉水瓶、塑料袋、一次性餐具,环保志愿者们不时来清理。
巨大的风车,切割高空的风,每次破空,划开一个口子,都有飞机掠过的声音。一些变化在正在高处发生,捕获、转变、存储,动能变电能,顺着地上地下的电网游走。

台风过后的海滩
捕风人
在木兰湾风电场打工的人,来自五湖四海,这些捕风人,顺着行业风向找生计,加入清洁能源领域“淘金”。
梁佐是其中一位,他 34 岁,河南人,开过 10 年的农用收割机,追麦收、追稻收,习惯了漂泊。成为风车运维工程师刚半年,从追逐作物的自然节律,转向了追逐能源布局的产业节律,新疆到海南,不停奔赴有风的地方,他已经跑过 4 个风电场。村里人都羡慕他,找了一份坐飞机到处跑的工作,“一边旅游一边打工”。
其中的枯燥辛苦只有自己知道,“游客觉得风车很美,我感觉不想看到它,一看它就是干活”。风车海岸的晚霞和银河在网上刷屏,梁佐没看过,“到那个点,我们都下班了”。
他的工作是给风车做保养,检查螺栓螺母。早上九点,从附近的镇子开车二十多公里,到木兰湾的风场。哪个风机不转,就是里面有人。

风车海岸
梁佐一进塔筒,就看不见阳光,也听不到风声,世界只剩机器的声音。塔高 120 米,坐电梯慢慢上去,需要 8-10 分钟。顶部的机舱是铁皮房,夏天将近 50 度,热得来“上不来气儿”,要喝藿香正气水防中暑。突然起风时,风机晃动,站不稳。累了随时坐下歇会儿,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自由,没人催,活儿干完就行。
塔筒的连接处,每层由 100 多颗连接起来,一颗螺丝就有几十斤,跟胳膊一样粗,螺母比拳头大。去年摩羯吹断了不少风车,每台价格超过千万元。再有台风来,风场业主总是很紧张,要求多检查一遍连接处。
对梁佐来说,刮台风就是休假,躺着领工资。秋季台风扎堆,一个月干不了几天活,工资也有六千多。一下班工友们都躺在宿舍,刷抖音,找朋友打视频电话,各看各的手机。
在抖音上刷视频,看到有人说因为附近有风场,玉米旱死了。他挺郁闷,回复了一张图片,是自己干活的风场,正好在玉米地旁,留下评论为风车正名:玉米长得挺好,跟风车没关系。
睡前躺在床上,手机里没什么好玩的,睡也睡不着,这时候他会觉得孤独,想家。梁佐想攒钱,给两个儿子买房,攒彩礼,“不能让他们打光棍”。
清洁能源转型,正孕育在每个普通人,每一次“拧紧螺母”的动作中。但梁佐很少去想环保那么远的事,这份工作的意义,对他而言非常具体,一份稳定的收入,以及一个清晰的盼头——等摸清了门道,梁佐计划着,加入堂哥的风车运维公司,自己招人、带团队,“这行缺口挺大的,知道的人很少”。
一位海上风电场的运维,印证了他的说法,公司一直在招人。行业在扩张,工作也辛苦,做海上风电运维,比陆地运维工资高一千,能拿到 7000 块左右。不过经常要住在船上,睡在海中,夜里船左右摇晃,身体和生活,随着风浪起伏。


海岸上焚烧旧物和钓鱼的人
吹又生
台风摩羯吹过的木兰湾,防风林光秃秃的,露兜树四脚朝天,贴着地面平行生长,海滩上多了枯树根、锈迹斑驳的机械、碎裂的木块,显出一片奇异的荒芜。被风推倒的生活,又在起草新的应答。
不是节假日,游人就很少。附近镇上的小伙结伴钓鱼,钓钩佛系地甩向大海,收获寥寥。两个女孩,在海边焚烧旧物,神色肃穆。
台风带走了美景,常驻 2 号风车观景台的小贩阿姨生意不好。她是附近的村民,自从两三年前,风车海岸变成了旅游胜地,她每天都来卖椰子、冰红茶和鸡蛋。秋季台风多,更是没人,好不容易来个顾客,挖椰肉的刀由于很久没用,找不到了。
附近一家小卖部,92 岁的奶奶独自看店,孙子打渔去了,只有一只叫小花的黄色狸花猫陪着她。“人都穷了”,她这样理解游客减少。盖这间靠海的小卖部,花了 10 万块,台风后冰箱、吊扇都打坏了,又花了 3 万重建。

刘星画作风车彩绘前,拍照的游人
推倒重建的,还有刘星的画作,他自称“流浪画家”,作品去年 8 月底在风车海岸上诞生,9 月就被摩羯毁了。他的画布就是木兰湾的风车,前前后后设计了 70 多个方案,冲浪、东郊椰林、卫星发射中心、灯塔,调研时边吃边找灵感,文昌鸡、糟粕醋,也纳入了设计。
绘画施工,经常在工厂完成,有时也要站在百米高空的吊篮上,感受失重,像要在空中起飞。更多时候,他负责指挥他人作画。工人离风车太近,看不见自己画了什么,刘星就站在 200 米外,拿着望远镜观察构图,再用对讲机提示:“再往上两个焊缝,是眼睛的位置”。
今年在新安装好的抗台风型风车上,刘星重画了旧作,风车彩绘再度立在海岸线上。网上又出现了打卡的照片和视频,拍星空的时候,人们会拍上他的巨画。艳阳天里自驾环岛下坡,游客发帖说,美到当场喊出来,“撞进了治愈系的电影里。”
大学毕业生江扬是当地人,他喜欢去风车海岸,拍照,放空,他住在附近镇子上,一个人骑车过去,十多公里路。
风车大而壮观,让人感觉渺小,可以安放一个年轻人的心事。高中时,同桌离开,他独自坐了一年半;大学时,三个人的小团体中,他总是被疏远的那一个。毕业后回到家乡,做自由职业,带游客赶海,其他时间就一个人呆着,习惯了孤独。
爸妈在镇上开修车的铺子,他们干不了多久,得靠自己养家。江扬想着,在木兰湾交通变发达之前,开一个租电动车的小店。骑车去海岸的路上,顺风时,像是被风托了一把,心事吹散了一些。

摩羯过境后,断掉的电线
风车发的电早已并网,无从得知它的去向,转化的风能,存在哪一块电池里,点亮了哪一盏灯,为减缓气候变化,贡献了多少能量。只能看到,它切实催生了微小的新秩序:一份生计、一件作品、一点慰藉。
附近村子的农妇,在风灾后新生的植物中,寻找草药蔓荆,捡一斤能卖 50 块。牧民来海边放牛,牛在厚藤中间挑拣食物。风车下一片狼藉的草木之间,新长出了白色和粉色的长春花。
风车匀速转动,生活迭代向前。在敬畏、承受、对抗、利用与共生之间,人们持续校准着与风的关系。风永远不会离开,与风口小镇的居民一样,世世代代在这里居留。
(为保护隐私,文中人物均为网名或化名。)

保护地热搜
- 《中国自然资源报》理论版刊发邓侃文章:做好固碳减碳的林业文章 | 阅142896
- 《中国林业》杂志刊发邓侃文章:解读“森林是钱库” | 阅122773
- 物种通用数据 | 阅21508
-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| 阅18382
- 唐雪琼:后新冠疫情期间的云南自然保护地社区生态旅游发展 | 阅15223
- 我国湿地现状如何?如何解读第25届世界湿地日主题? | 阅14648
- 中国七成河蚌濒危或极危,90后小伙编著《河蚌》呼吁保护 | 阅12405
- 日本国家公园保护管理观察 | 阅11859
- 红树林该如何保护才科学 | 阅11687
- 2023年生物科技趋势:合成生物占据“C位” | 阅11575
| 我也说两句 |
| 版权声明: 1.依据《服务条款》,本网页发布的原创作品,版权归发布者(即注册用户)所有;本网页发布的转载作品,由发布者按照互联网精神进行分享,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无商业获利行为,无版权纠纷。 2.本网页是第三方信息存储空间,阿酷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,服务对象为注册用户。该项服务免费,阿酷公司不向注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。 名称:阿酷(北京)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:李女士,QQ468780427 网络地址:www.arkoo.com 3.本网页参与各方的所有行为,完全遵守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。如有侵权行为,请权利人通知阿酷公司,阿酷公司将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删除侵权作品。 |
 m.quanpro.cn
m.quanpro.cn
